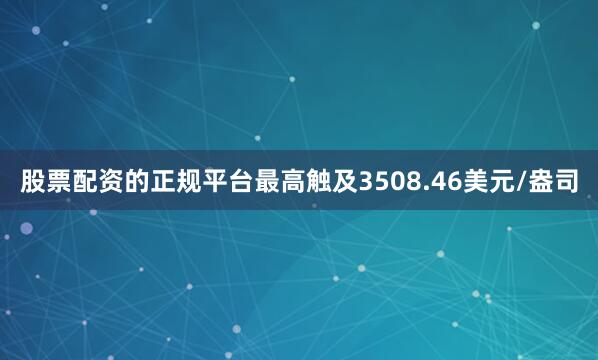军旅铁嗓为啥“退到幕后”?人民日报点名后,他的真日子没那么简单?

说句掏心窝子的话,这位在舞台上穿军装、嗓门儿一开就顶天立地的人,如今被人民日报点了一回名,不是夸两句完事,反倒把他的“真实处境”给照了出来。你可能会问,阎维文,这不一直是“国民歌王”“军旅铁汉”吗?地位有、名气也有,他还能有什么难?别急,咱慢慢聊,越往下看,你越觉得这事儿,有点意思。

他自己最爱说一句话:我不是明星,我就是个唱歌的兵。听着像客气,懂的人知道,那是他这辈子的路数。1979年进了总政歌舞团,年轻气盛,结果一看周围,哎哟,能用意大利文唱咏叹调的大有人在,他当场就“蔫”了。咋办?老办法,硬练。白天训练、晚上关着琴房不出来,一年就从合唱里蹦出来当领唱,1984年唱《小白杨》,算是真出了圈。到这儿你以为剧情该是一路开挂?没有,他把最好的场子,全给了基层部队。

你想想,谁会一年往边防、哨所、革命老区跑上百场,还不是去走个过场,是真把那儿当家。1983年他第一次上西藏边防线,海拔五千多,缺氧到头疼炸裂,上台前还一脑袋撞门框,整个人嗡嗡的。歌一唱完,台下掌声呼啦啦,战士们黑红的脸笑得跟花儿似的。那会儿条件苦,维生素都缺,战士们把舍不得吃的绿色菜全端出来。这一幕,听着就热乎,他自己说,那一刻把“为最可爱的战士唱歌”刻到了骨头里。

再往后,1985年中秋,他跟几个艺术家上了老山前线。炮一响,猫耳洞里落灰,大家心里直打颤。到了昆明军区总医院,手术室里三张床,白床单底下,是被炮火烧得不成人形的年轻命。说实话,我看到这段也愣住了。他哽咽着把歌唱完,回北京后跟团里说,不提房子了,这点待遇和前线比,算个啥。你说,很多人嘴上讲初心,这位是用见过的血和泪,把“初心”给按实了。

有人可能会好奇,他咋就这么能扛?这还真不是天降神力,是从小时候就走了弯路、吃了苦头。小学一年级,靠快板书的嗓门被老师盯上,13岁进了山西省歌舞团,结果被分去学舞蹈。问题来了,人家天生身体硬,劈叉都难。他呢,午休、晚饭后全拿去练,练到坐骨神经痛,腿只能折成90度。歌舞团老师教他狠招:每天把腿硬掰过90度,挺20分钟。两个月,咬着牙,硬是把病练“回去”。这股劲,你说不服都不行。

说回今天。9月11日,他在人民日报写了篇《工夫在诗外》。这标题,你看着文气,我给你翻成大白话——台上那点招儿,不够,背后得有日积月累的修炼。他给年轻的民族声乐歌手提了几件扎心事:很多人开头唱得挺好,越唱越崩,紧张只是表,技术是里子;比赛爱挑大部头,结果扛不住,现场翻车。还提到一个现状:民族声乐的观众偏老,这路子再不拓,迟早“断代”。他给的路数很直白:基础打稳,眼界放大,文化修养跟上,再把流行的东西学点儿,别端着。你要问这话靠不靠谱?前辈李双江早就说过,“最好的唱法是用心歌唱,不是拿技巧炫。”这两位的共识,基本把行业风向点透了。

说到这儿,另一个反常识的地方来了。舞台上他是铁血硬汉,回到家,脾气软得像棉花。他跟妻子刘卫星,青梅竹马,十四五就认识。部队那会儿谈恋爱可不行,两个人还是悄悄守着这份感情。婚后第二年,他忙,妻子独自回山西把女儿生了。后来千方百计把妻子调到北京,就在总政歌舞团附近上班。他只要在家,就接送上下班,中午还送饭。听着平常,真正难的是后面这段。

1988年,妻子查出乳腺癌,没到30岁。你换谁,脑袋都嗡。那时候他要去参加比赛,他说不去了,守着妻子手术。妻子反倒把他往央视门口送,冒着瓢泼大雨,说:你走吧,你这路走得不容易。那年他唱《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》,拿了金奖。别急,1992年,病又复发了,癌细胞转移。他在军艺读书,扭头退学,剩下的时间全陪着,热疗、放疗,天天医院里守着输液。说句实在话,这种陪伴,不是嘴上说“我愿意”就能做到的。更意外的是,病情三次转移,最后竟然挺了过来,医学上都说少见。他现在走哪儿都带着妻子,就怕她一个人瞎想。心愿很朴素:等有空了,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,把错过的风景补回来。你听着是不是也被戳到了?

家里头,女儿阎晶晶也是有主见,在加拿大学设计,毕业后没在国外拿高薪,直接回国,这份选择,很多父母看了都松口气。女婿李禾禾,来头不小,是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公子,海归学霸,哈佛双学位。你可能会吐槽,这婚姻“名门望族”,够体面。可你要细想,体面背后,更多是两代人对“家”的那点笨拙的坚持,既走正道,也讲担当。

有人会问,人民日报给他发文,这不就是地位坐实了?话别说满。名与利这俩玩意儿,真救不了一个把自己一辈子扎在军歌里的老兵。他面对的难点,是民族声乐受众老龄化,是年轻人“眼高手低”的赛场风,是商业演出和基层舞台的两难选择。你说去商演,多挣钱、曝光高;你说扎基层,苦不说,传播还慢。很多艺术工作者在这条路上摇摆,他的选择是“部队是家”。这不是更高尚,是更笃定。也正因为这样,他在人民日报说“工夫在诗外”,才显得有底气。不是站在云端讲道理,是从高原缺氧、前线炮火、病房消毒水味儿里走出来的人,在唠心里话。

说点行业外的人都感兴趣的现实吧。现在的年轻歌手,参加比赛像打游戏,一首首大部头往上堆,花里胡哨,转音一套接一套。舞台是热闹了,观众记住谁了?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,唱到后半程气虚、情散、字也糊。这就是他嘴里说的“技术断档”。这事儿怎么破?别嫌土,绕回去打根基,气口、咬字、情绪线,这些基础活儿像修地基,藏在地面下,别人看不见,房子是否结实,全指望它。再加一条,别把民族声乐关在屋里,和流行借点手,旋律、编配、舞台表达上试试,年轻人就爱新鲜感,老艺能也不是古董,活在当下,才有下一代观众。

说回他的人生脉络,你能看出三条线拧在一起:军旅的初心,专业的苦功,家庭的担当。边防线上的掌声,是他的精神底盘;琴房里的日复一日,是他吃饭的本事;病房里的那盏灯,是他做人那杆秤。有意思的是,这三条线不是互相拖后腿,反倒互相撑着他往前走。你看,前线回来,他把待遇看轻;家里出事,他把学业放下;舞台上,他把“炫技”按住。这些选择,都不体面,但真“厚道”。

你可能还想知道,李双江多年前说那句话——“最好的唱法是用心歌唱”——放到今天还好使不?依我看,不光好使,还是硬通货。技术可以进步,审美会变化,观众会换代,只有“用心”这件事,是穿越时间的。阎维文这一路,就是把“心”拿出来,给边防、给战友、给妻子、给歌。这样的路径,未必人人能学,也未必人人愿学,可一旦走通了,舞台上就会有一种“站得住”的安静力。你说是不是这理儿?

当然,话说回来,商业社会的车轱辘已经轰隆隆开上高速,文艺工作者守着基层,是不是会被时代边缘化?我不敢下死结论。我的想法是,谁都要吃饭,谁也想被看见,关键看你“为啥唱”和“唱给谁”。只图热闹,热完就散;守着本心,慢火熬出味。两条路都有人走,哪条更难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。

写到这儿,点几个你可能会关心的现实问题,咱开开脑洞:

你觉得民族声乐要不要和流行深度“打个照面”?守规矩和出圈,边界在哪儿,咋拿捏?

面对比赛里的“眼高手低”,评委、平台、学校,谁该先动手去改比赛风气?

如果你的另一半突遇重病,你会不会像他一样,放下学业或者工作去全力陪伴?值不值,这账咋算?

权威媒体的背书,和大众审美的认可,哪个更重要?要是打架了,艺术家该站哪边?

留言区咱们唠唠,别客气,讲讲你看到的、经历过的、想不明白的。说到这儿,我的态度也摆这儿了: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,这话老土,可真理就这味儿;为人做事,笨一点没啥,稳、厚道、扛得住,才是长久的路。你觉得呢?

对了,有个细节别漏了。那篇《工夫在诗外》,不是教条,是一个从西藏边防到老山前线、从昆明军区总医院到北京、从山西到加拿大再到家的男人,在不同时间点给出的“活法总结”。1983年的高原缺氧、1985年的炮火冲击、1988年和1992年的病房守候,这些坐标把他钉在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里。也正是这些现场,撑起了他今天的那句“唱给谁听”的底气。这就叫,人生不怕慢,就怕没方向。

行,今儿就聊到这儿。愿每个在台前台后用力活着的人,都能被看见一眼。你说,是不是这么个理儿?

天载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